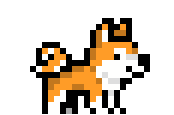胡萝卜和驴
宇宙探索编辑部
很久之前就想看宇宙探索编辑部 (2021),郭帆监制,还出镜客串了一下。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魔幻荒诞、有点黑色幽默,很是喜欢。剧情就不细说了:
唐志军(杨皓宇 饰)是一家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现如今的杂志社日渐式微,唐志军也终成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但他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终于有一天,他接收到了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一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再一次踏上寻找外星人的旅途。
在未来的我与过去的我这两条时间线里,我准时准点的看了这个电影。以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如不是这样,我就不存在了,我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既看了这部电影又没看,这是我区别与其他任何在发生的事情的不在场证明。
但诸如此类的许多如此确定的事,我们却往往无法证明:比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现在就是处于既是又不是的状态。人们总爱说时间会证明一切,但它就像一个河边垂钓的老头,除了沉默的看着你,你也看着它之外,它证明不了任何,也没义务做其他事情。直到你也和它一样成了老头坐在河边,你又如何能让几十年之后的你,现在开口对你讲话。
胡萝卜和驴
电影里最荒诞的一幕,我认为也是叙事高潮的地方,就是唐志军居然真的顺着孙一通与外星人沟通的线索,碰到了村子不见的驴,骑了上去。不得不佩服编剧和导演的艺术表现能力,不夸张的说,电影里的这种故事我梦里做过的,要比它精彩的多,但我拍不出来,也写不好。最近正在研究一个新项目:墨菲斯·弗洛伊德·周公,通过文字描述和相关图片来生成动画视频,打通梦境与现实。

胡萝卜和驴这个隐喻很好理解,关键是:到底谁是胡萝卜,谁是驴。
对于一直在找外星人的唐志军来说,可能外星人就是胡萝卜。对于人类来说,形而上学、自由意志、甚至科学与未知,可能也是胡萝卜。
电影的最后,这次寻找外星人的旅途之后,唐志军也完成了自己内心对于女儿的死、自己科学与外星人执着的自我救赎,导演借唐志军的口说到:
其实我们人类一直没有弄明白,宇宙是为什么而存在,我们人类又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
这个答案不在外太空,不在宇宙深处,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原来我们每个人既是存在的谜题,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就是DNA)
…
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首宇宙之诗里,读懂我们存在的意义。
一段从地球到太空、银河、星系的缩放,电影最后定格在一组DNA的图像,完。



在山洞里,唐志军问孙一通,外星人再和你联络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知不知道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孙一通说:可以。但如果外星人也不知道呢,如果他们也对自己有同样的疑问,来地球就是想问我们这个问题呢。
顺着这个思路,就好理解编剧和导演在电影结尾想说的了:生命本身就是存在,就是意义本身。人类的基因在地球形成亿万年之后得以复制到今天,避开了所有可能毁灭人类的概率事件,人类的历史就是意义。刻在基因里的,传承、复制,夹带着从人类诞生开始的最原始的信息,并一直延续下去,这就是基因本来的目的,这就是生命。寻找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那个胡萝卜,同样也是人类对美好的追求与希望、探求真理的好奇心(唐志军不止一次说到:有好奇心,是好事)。
我一直不习惯说的这么宏大和乐观:基因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跟耶稣的职务挺像。它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导演其实也说了:完成繁衍之后的所有的性欲,都是一种疾病。

壁垒
唐志军这个人物在电影中,是一个连暖气片钱都快交不起的“失败者”,执着于寻找外星人,他说:当人类得知有外星人存在的时候,之前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隔阂都会消失(一起对抗外星人文明),所以让人类文明进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讽刺拉满。
电影中无时不刻,唐志军都显得与外界格格不入。但其实他说的话和科学家没什么两样,做的事也没什么两样。也曾经成功过。
这种格格不入的“不正常”是一个壁垒,一个他本人要打破的自己的壁垒:用成功证明自己或是结尾对自己的救赎;但更大的壁垒是与外界的,知识与认知的壁垒;再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壁垒、理论与实际的壁垒:完成繁衍之后的所有的性欲,都是一种疾病。这句话百分百正确,但没啥用。(只有人类会形成道德伦理的框架,并在此之上把理性的、规范化的基因复制体现的那么美好。) 这种戏剧冲突与隐性的矛盾带来了极大的喜剧张力。这种黑色幽默,电影诠释的太好了,余味拉满。
现实里,这个壁垒就不那么好打破了,特别是知识与认知的壁垒。就算爱因斯坦亲自跟我讲相对论,我也听不懂,也无法很快相信。但如果爱因斯坦告诉我,经过我相对论的计算,现在这个链接拼夕夕砍一刀,可以立省9.9!我打开链接的可能性高达70%,尽管相对论和拼夕夕能砍多少好像没啥关系。世界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同样需要秦始皇、马斯克、乔布斯这样的“暴君”与“演说家”。
乔布斯的一句名言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iPhone出现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It’s really hard to design products by focus groups. A lot of times,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until you show it to them.
根据受众需要去设计产品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是需要你去展示给他们看。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顾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 乔布斯
科学家发现、研究、揭示胡萝卜的本质,演说家包装胡萝卜的表象。奥本海默好像把这两个事都做了,基因也一直把这两个事都做了。
面前的那个胡萝卜,和多巴胺很像。有时候甚至不想让自己取下那个胡萝卜。(总是拿多巴胺当我的反面例子其实挺抹黑它的)更多时候,是压根不会知道那个胡萝卜是啥,在不在面前。
真正的替罪羊,我为自己找好了:如前面所说,这都要算在基因的头上。
剩下的就是:一直热爱我的热爱。它真是个胡萝卜也没办法,毕竟基因使者说了算。
杨绛曾在回复一个青年的信中写道: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事实确实如此,但另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我们自认为比一般人读了更多的书之后,我们会认为比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也更多了一点。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当我们觉得无知的欢乐胜过知识的累积时,我们如何正视自己以及自己所读的书呢?勒内·夏尔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 “理解得越多就越痛苦,知道得越多就越撕裂。但他有着同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
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想悲壮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则愿意为了理想苟且偷生。
—《麦田的守望者》
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同意。
为什么越看他,越觉得今天的演员没文化 - 王志文 08:43 他的真诚再外界看来倒成了一种固执。
我爬炉筒时, 大概是九岁到十一二岁。 到了四十岁上,我发现后来我干任何事情都没有了那股百折不挠的决心 ;而且我后来干的任何事都不像那件那样愚不可及。爬炉筒子没有一点好处, 只能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 但我还是要爬。这大概是说明你干的事越傻,决心就会越大吧。这也说明我喜欢自己愚弄自己,却不喜欢被别人愚弄。
— 王小波《黄金时代》
“I see a lot of people with talent but the one thing they don’t have is that just love of doing it for the sake of it.” — Rodney Mullen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有天赋,但有一点他们没有,那就是他们只是为了热爱而热爱"。 — 罗德尼·马伦
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约翰·克里斯多朵夫》
看到和菜头的这篇:驴前萝卜 ,想起来之前也写过类似的,加上。之前图床的图片也失效了。 –202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