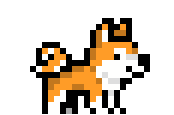三颗大包菜

书的香味
好几天没吃有机娃娃菜了,思来想去,还是它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食物中脱引而出。买完菜回来路上,看到一个摆着许多书的大摊子,支棱起来的简陋的棚子上面挂着一个牌子,醒目的写着:全场图书,买二本送三本。
老实说,不是这个牌子,我今天是应该不会走过去的。我也一贯没觉得自己的热爱足以给我不加思考就不自觉行动的动力。如果我是因为热爱读书,喜欢看王小波的书,在白嫖完电子版之后我应该早就在书店买了精装版,而现在却是在一个图书大甩卖的街边小摊,而且很可能是盗版。开始写标题和日期的时候才发现,今天正好是315。
就看书这个事,有必要多写几句。我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从我看过的书那少的可怜的数量就足以说明。但是走过路过书店,总是会不自觉看一眼,但又很少走进去。为数不多的进去书店的时候,也只是翻看翻看书皮,正过来看又反过来看,回忆起来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在干嘛。只记得,印刷书的油墨味道好闻,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巴适,还有把纸张翻页过去,手指摩擦纸面的触感,这些总在我看到书的时候不自觉的被调动起来。如此说来,我对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书的内容和书这个承载知识的载体本身,这个兴趣的源头极有可能是因为无聊。
三颗大包菜的分量
买了时代三部曲和其他几本看过的觉得不错的就走了,一共140元。
这六本还是有点沉的,大约是三颗大包菜的重量。四舍五入,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一生现在也就约等于三个大包菜。
在那个书摊上,还有许多很有分量的书,比如:《穷查理宝典》、《纳瓦尔宝典》、中国四大名著、《白夜行》等东野圭吾小说,再就是儿童图书和一些畅销书。整个书摊大概三百本左右,如此分量,一个简陋的书摊架子足以,因为书摊架子只会不自觉的提供向上的支持力平衡书的重力,这对于铁架子加上厚木板的组合太轻松了。
也因为书架不会看书,所以只能本能的、不自觉的提供材料的支持力和张力,感受到书本的物理重量;而我会看书,除了提供把书拿起来、翻页之外好像也没多少其他我这个材料本能的、不自觉的力量,况且三个大包菜的重量我已经觉得沉了。因此我远不如一个三百本也不费吹灰之力的书架。但在路过书店这个事上,我比书架做得好,我自觉的就像不自觉一样,这是书架做不到的。
王小波的书放在书摊里不起眼,这个不起眼有三:和中国四大名著放一起的不起眼,和《穷查理宝典》、《纳瓦尔宝典》,还有和育儿、儿童书放一起的不起眼。四大名著自不用说,这是正统文学文化根基的分量,《穷查理宝典》这是教人致富的财富分量、名人典型的分量,育儿、儿童书、畅销书这是生活消遣、童趣的分量(今天书摊里看的人最多的也是这一块)。对于我这种没有看书“不自觉”的人来说,更不起眼,很可能以前在书店已经路过王小波的书许多次了。
我今天买这些书的行为可能在我读了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作家、文学创作者,跳出了艺术创作的体裁本身,这正是我现在在思考和践行的过程。我既想看看王小波的答案,更想找到新的自己的答案。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 举个例子说, 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生的译本。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 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 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 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 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 假如没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 :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 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 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 样的小说相比。
引自“用一生来学习艺术”收录于《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真想看看王小波写的这个时代。
李志被禁言了,《黄金时代》王小波被删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是几颗大包菜不起眼的躺在书架上呢。